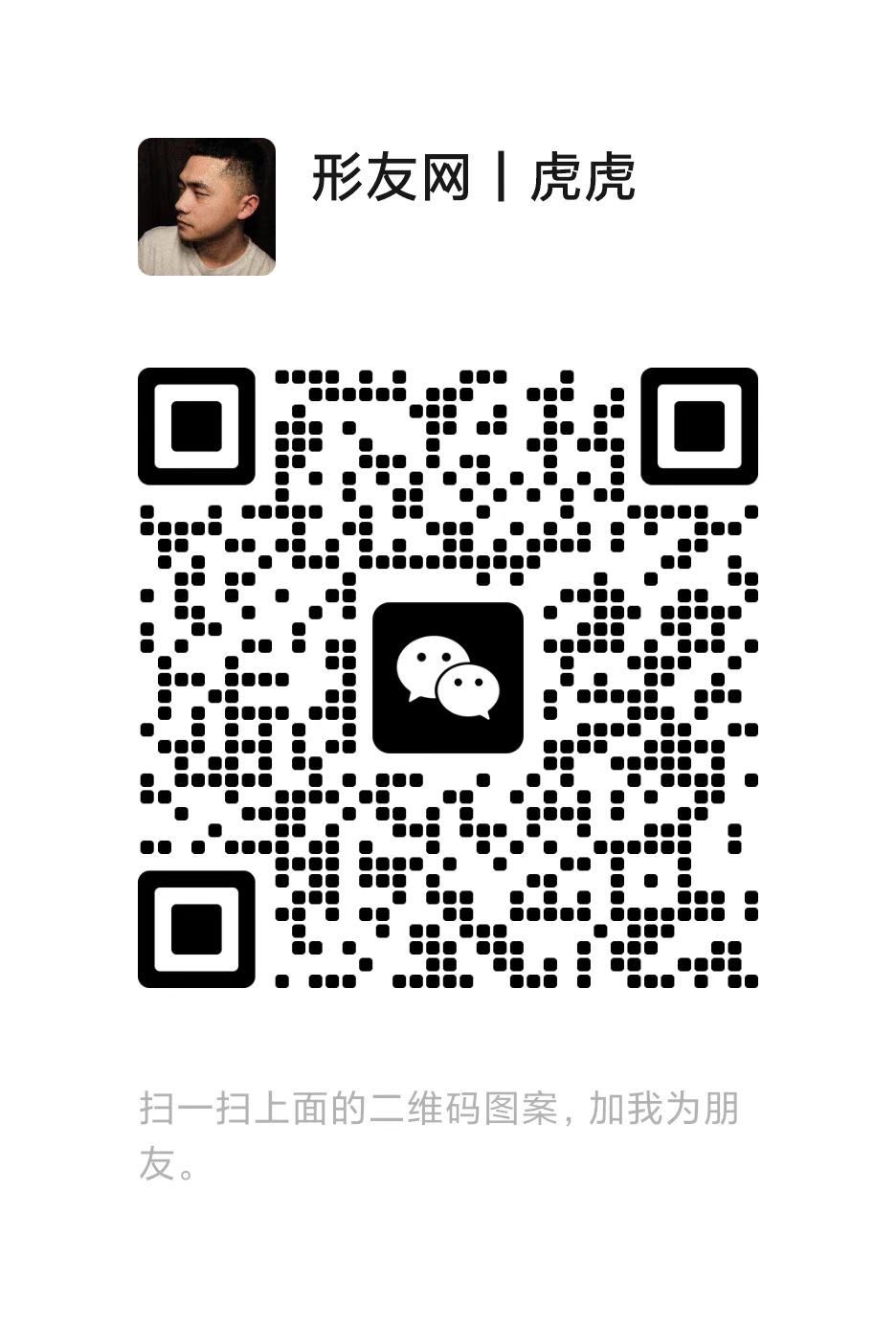清晨推开窗时,总会看见对面楼顶的那丛瓦松。它们从水泥缝隙里钻出来,带着灰绿色的叶片,在风中微微摇晃。去年冬天那么冷,我以为它们早就冻枯了,可开春第一场雨过后,竟又冒出星星点点的嫩芽,像一群举着小拳头的孩子,执拗地向着天空生长。
清晨推开窗时,总会看见对面楼顶的那丛瓦松。它们从水泥缝隙里钻出来,带着灰绿色的叶片,在风中微微摇晃。去年冬天那么冷,我以为它们早就冻枯了,可开春第一场雨过后,竟又冒出星星点点的嫩芽,像一群举着小拳头的孩子,执拗地向着天空生长。这让我想起老家院墙上的爬山虎。小时候总觉得它们是最有耐心的植物,春天抽条时慢吞吞的,几片嫩叶在砖缝里试探着伸展,仿佛生怕惊扰了什么。可一旦缠上了木架,便开始疯长,卷须像无数只小手,抓住阳光就能攀爬。到了夏天,整个墙面都被染成浓绿,暴雨过后叶片上挂着水珠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,倒像是它们笑出的眼泪。
楼下的月季花丛更是有趣。去年秋天被台风刮断了主枝,只剩下半截光秃秃的枝干戳在土里。邻居都说这花活不成了,我却看见断口处慢慢鼓出小小的芽苞。如今那些新芽已长成半人高的枝条,顶端缀着饱满的花苞,粉白相间的花瓣裹得紧紧的,像一个个攥着的希望,只等某个晴朗的早晨,就 "噗" 地一声绽开笑脸。
小区里的流浪猫也透着股乐天派的劲头。那只三花猫总爱在车棚顶上打盹,阳光好的午后,它会把自己摊成一张毛茸茸的饼,四脚朝天露出雪白的肚皮。有次我看见它追着落叶跑,踩空了从矮墙上摔下来,打了个滚就爬起来,抖抖耳朵继续追,尾巴翘得老高,仿佛刚才的狼狈只是一场有趣的游戏。
菜市场门口的修鞋摊,摊主是位姓王的老爷子。他总是笑眯眯的,左手捏着锥子,右手扯着线,嘴里哼着跑调的评剧。有回下雨,他的帆布棚漏了水,老先生不急不忙地挪到屋檐下,掏出收音机接着听戏,还跟避雨的路人开玩笑:"你看这雨下的,正好给我的针线洗个澡。" 他的修鞋箱里总放着块薄荷糖,谁来修鞋都要塞一块,说含着糖干活,针脚都甜丝丝的。
公司楼下的早餐铺,夫妻俩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忙活。女人揉面时总爱哼歌,男人炸油条的动作像在跳舞,面团在他手里转个圈,"滋啦" 一声跳进油锅,很快就膨成金黄的样子。有次我问他们累不累,女人擦着手笑:"累啥?你看这油锅冒的热气,多像咱们日子里的烟火气,蒸蒸腾腾的才带劲。"
上周去郊外徒步,遇见一群写生的老人。他们坐在山坡上,对着远处的云海涂抹颜料,有位老太太的画架被风吹倒了,颜料洒了一身,她却拍手笑起来:"你看这蓝颜料蹭在裤子上,倒像是把天空穿在了身上。" 夕阳西下时,他们收起画具,互相搀扶着下山,笑声比林间的鸟鸣还要清亮。
街角的盲人按摩店,每天都飘出淡淡的艾草香。按摩师是位三十多岁的姑娘,说话时总带着笑意,听脚步声就能分辨常客。有次我问她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穴位,她笑着说:"闭着眼睛的时候,手指头就变得特别灵,能听见经络在唱歌呢。" 她的工作台边放着一盆绿萝,叶片总是油亮鲜绿的,据说都是她用手指摸着浇的水。
楼下的幼儿园里,孩子们的笑声像刚开瓶的汽水,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他们在沙池里堆城堡,被风吹塌了就拍手叫好,说要盖一座更大的;他们追着肥皂泡跑,泡泡破了就仰起脸,看阳光在自己脸上投下的光斑,以为那是泡泡留下的吻痕。老师说,有个小男孩总爱捡地上的梧桐叶,说要把秋天夹在书里,等冬天的时候看,就能想起阳光的味道。
傍晚去公园散步,常看见一对老夫妻在跳交谊舞。老先生的腿不太方便,迈步时有点瘸,老太太就配合着他的节奏,脚步迈得又轻又慢。他们的舞姿算不上标准,却像两棵相依的老树,根在地下紧紧相连,枝叶在风中互相致意。休息时,老先生会从布袋里掏出保温壶,给老太太倒一杯菊花茶,花瓣在水里慢慢舒展,像他们脸上缓缓绽开的皱纹。
前阵子整理旧物,翻出大学时的日记本。里面夹着一张银杏叶,是某个深秋在图书馆门口捡的。当时正为期末考试焦头烂额,看见满地金黄的落叶,突然觉得那些烦恼就像叶子上的纹路,看着复杂,其实都是阳光走过的痕迹。如今再看那片叶子,边缘已经有些发脆,却依然保持着舒展的姿态,仿佛还在诉说那个午后的温暖。
其实生活就像这自然界的万物,总有阴晴圆缺,可只要心里住着阳光,就能在风雨里长出铠甲。瓦松在石缝里扎根,是相信雨露会如期而至;猫咪从墙头摔下仍不气馁,是懂得快乐比体面更重要;盲人姑娘能听见经络的歌声,是因为她把心变成了眼睛。
就像此刻窗外,夕阳正给云朵镶上金边,那丛瓦松的叶片被染成暖橙色,像是披上了阳光织成的披风。风过时,它们轻轻摇曳,仿佛在说:你看,黑夜再长,也挡不住黎明要绽放的光。